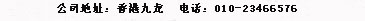学思书评文化人类学系列疾病隐喻与反
—文—化—人—类—学—系—列—
疾病隐喻
与反对阐释
——《疾病的隐喻》书评
提到疾病,我们很容易产生恐惧和恐慌心理。疾病唤起了我们的负面情感,让我们联想起死亡、灾难等一系列不好的事。人们似乎无法接受这个必然的自然现象,而须为之寻找合理的解释。对不甚理解的事情人们只能通过隐喻谈论,结核病曾经被认为是贵族病,咳嗽让人更加有趣、更有风度,梅毒和艾滋被附上道德的批判和政治的诉求,而癌症作为一种异化的象征,从自身生长并吞噬自身……
年伊始,新冠病毒大面积爆发,大家一方面为这场“战疫”所全民调动和感动,一方面又对带湖北的车牌避之不及,让在外地的武汉人成了过街老鼠;到后来病毒起源的舆论政治化,特朗普直接推锅“中国病毒”,我们发现,疾病并非简单的事实,它会被不同利益出发点的角色进行不同的阐述和演绎,而这本《疾病的隐喻》为我们重新看待疾病在社会层面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
一、作品简介
苏珊·桑塔格(—)是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是二战后美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被人们称作“美国公众的良心”。《疾病的隐喻》是苏珊·桑塔格称两篇批评性文字的合集,第一篇《作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写于年,第二篇《关于艾滋病的隐喻》(《AIDSandItsMetaphor》)完成于年。写《作为疾病的隐喻》的时候,桑塔格正在经受癌症的困扰。所以,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做是她有感而发的产物,也是她的“现身说法”。
这两篇文章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评论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都是考察疾病(特别是那些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艾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恶性肿瘤,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正因为桑塔格自己身患癌症,所以她对将疾病隐喻化所带来的后果自然也就更深刻一些。她在文章中提到的疾病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受人待见的病,尤其是不易治疗又容易传染的疾病,病人往往还没有在身体上死亡,其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谴责就已经宣判了他们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性死亡”。得病本身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但一旦社会将所得之病“隐喻”化后,患者本人就不光要经受身体上病魔的摧残,更要面对社会上诸多疾病以外的压力。这也正是桑塔格为什么要写这样两篇文字来批评被隐喻化的疾病,她所要做的就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
二、疾病隐喻何以产生
疾病本身让人恐惧,因为它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使人类的活动受到限制,更进一步的甚至让人丧失生命。而患病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弱者”,成为了潜在的被欺负者和可获利者。一个人患病之后,对于亲人来说是巨大的悲痛和沉重的负担,对于社会来说是劳动力的丧失和福利的负担。所以,许多关于疾病的隐喻往往是负面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心理健康。
我们平时并没有在意社会、文化会给疾病带来隐喻,我们以为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我们用来描述疾病的词汇,甚至于对疾病的理解都是客观的、再正常不过的。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们日常所说的对于疾病的态度、词汇、理解都是带有阐释性的,蕴含了大量的隐喻,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
作者揭露结核病与癌症等这些人类的普遍疾病被隐喻过度阐释并贴上了诸多符号标签的现象,如:
结核病:雅致、敏感、忧伤、浪漫、柔弱,是活力过分消耗的疾病。癌症:冷酷、无情、畸形、混乱增长,是能量失控的疾病。梅毒:羞耻、粗俗、渎神、是不正当性关系导致的群体泛滥的疾病。鼠疫:社会混乱、污染、反常的瘟疫。麻风病:社会腐败、道德败坏、邪恶、惩罚性的瘟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深信存在着一些特定性格类型的人,容易患上对应的疾病。如果一个人患上某种疾病,那么他也就背上了社会、文化所赋予的这些隐喻。
疾病隐喻大部分是医生、文学家、政治家促成产生并传播的。亚里士多德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萌芽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很不完全,人们将不认识的事物以熟悉的事物作类比,由此产生了隐喻的表达;在文明的繁盛期,文学家洞察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大量的隐喻被用来描述人类那些无法言说的感情,疾病的隐喻在此阶段也非常广泛;在现代社会,随着各种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对疾病隐喻的表达也是随之改变的。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样,“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但由于结核病逐渐被攻克和癌症的后来居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结核病来隐喻什么了,反而“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和消弭”。至于现代社会,较为活跃的疾病隐喻还有癌症、梅毒、艾滋病等。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医生“军事化治疗”的方法和政客“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的政治宣传也极大促进了疾病隐喻的传播。
三、疾病隐喻的诗学
作者主要通过结核病和癌症这两种疾病阐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隐喻,非隐喻性的科学病理的定义并不能被人们接受为满意的解释,只要人们谈论起它们,这两种疾病就带有了复杂的、多义的隐喻性思考。
在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结核病是分解性、发热性和流失性的,能带来高涨的情绪、好的胃口和旺盛的性欲,可以加速生命、照亮生命,甚至使生命超凡脱俗的意义,与其平庸的健康状态完全不同。它甚至成为19世纪中叶新中产用以确认自身地位的方式——痨病是优越的、有教养的、甚至是有文化的,瘦弱的身体楚楚动人,而其死亡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隐喻构建了审美经验,贵族阶级定义审美,又将这套审美价值观推广至大众。
结核病也成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归宿,具备与其诗歌具有一样敏感而优雅的风格才不失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审美价值。尽管疾病会使一个人备受折磨,但结核病是一种贵族病,是一种有浪漫色彩的艺术家会有的病,艺术创作一刻不停才会面色苍白无力,而因为咳喘脸颊通红,这又成了美的象征。
苏珊·桑塔格援引并考察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形象,包括了《悲惨世界》中的妓女芳汀、《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爱娃、《董贝父子》中董贝的儿子保罗等等。她说:“死得太美好了”是对那种天使般一尘不染心理学的肯定,当拜伦说:“我看上去病了,我宁愿死于痨病。”传递出的是一种浪漫主义,而对于死亡的这种浪漫主义变成了个性。”而另一方面,结核病为那些道德沉沦者提供了一种获得救赎的死法,《悲惨世界》中的年轻妓女芳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救赎,甚至当染上这种疾病而命在旦夕时,病人的道德境界飞升到了新的高度,《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天里恳求她的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释放他的奴隶。而在东方艺术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肺结核”美学。比如林黛玉、林徽因,几声咳嗽总能引来男人们难以捉摸的眼光。
结核病被用来描绘某个人死亡之美好,在隐喻对疾病重重包围之下,健康倒变成陪衬,变得平庸、不值一提了。但像癌症这样的疾病,就不那么幸运了。癌症被类比为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而在道德层面疾病具有惩罚性意义之外,其疾病隐喻还表现在社会层面上。人们认为患者缺乏精神能量,从而导致了疾病;而精神能量缺乏的原因,则是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将疾病归咎于现代工业,归咎于城市的现代化的不良生活方式:空气的污染、不良的作息、精神的消耗。
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将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全都看成是“致病的环境”和不良的诱因。自然成为一种隐喻,一个回归健康、回归原始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有乡村、自然,那些原始的地方,才能让人们摆脱“现代病”,回归健康,而“现代化”就等于不健康。所以十九世纪发明了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以离弃城市的方式找回身体的秩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也变成了癌症的一种隐喻,“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
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社会自身的问题才导致人们无意识中赋予疾病以隐喻、意义,并使得这些隐喻加害于患者。
四、疾病隐喻的政治学
除了疾病所引起的修辞意义,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疾病隐喻在政治上的泛化。疾病不再单纯地指代疾病,还用来指代一切消极的、有悖于自我意志之物,并带来“自我”与“他者”的隔离。
瘟疫自古被当作上天对一个共同体的惩罚,所以推到他人身上总是第一要务,结果成了沙文主义的催化剂。梅毒在英国人那里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老说是日耳曼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艾滋病被认为是从非洲开始,而非洲学者认为是美国的病毒武器,意在减少非洲的出生率。瘟疫总是带着异邦的邪恶想象,正如同近日新冠病毒在西方世界被称为“中国病毒”。当西方在污名化他者时,就已经预设了自身“道德完美”的状态,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或是认可的便被认作“异己”。
然而更可怕的隔离还不仅限于国家与文化,疾病之隐喻还被用于政府话语。要彻底根除社会制度的顽疾,就必须将疾病隐喻以最为恐怖的方式加以形容。希特勒将解决“犹太人问题”比作癌症治疗;中国将“四人帮”比作社会的“毒瘤”;直至今日,激进主义者和环保人士仍然把人类比作“地球的癌症”,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癌症恐怖隐喻的传播。就此,在政治学术语上,疾病成为了与自己的主张相悖的政治思想的代名词,成为了一桩“邪恶”。
可是,当矛盾被以“毒瘤”“沉疴”来命名时,其背后的问题或许早已并非简单的概念所能概括。意识形态和医学相互渗透,难以分割。疾病的政治学话语又返回医学之中,形成更大的恐慌,并维护意识形态自身的正义。疾病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减少疾病威胁的行为则被称作战斗或抗争,谈起“抗击病菌”或是“征服疾病”的同时也是在彰显政府的能力和权威。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
错误无可言说,而悲哀的患者却成为一切灾难的替罪羊。所有人将自身之外的不可理解和异己之见全都归咎于他,而他则无辜地承受了所有人的责难。伴随着对疾病的恐慌,患者被认定负有某种道德上的责任。与消费主义相呼应,患者的染病被看做是对他们自己不检点行为的惩罚:癌症是由于抽烟、长期的污染,或是过度的精神压力;结核病,和酗酒、堕落相联系;艾滋病是性生活的放肆。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的最高理想,应当遵循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循规蹈矩,勤劳,情绪自控,理性。而一旦有人越出了这条轨道并遭遇命运的不测,便被视作是堕落。
由此,隐喻使人们对疾病的倒错观念合理化,甚至转变成经验,最后经验又变成知识。但这些知识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幻象,疾病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偏见(Prejudice)”和“归因(Attribution)”,我们对疾病的错误归因和对患病者的偏见使我们将各种疾病隐喻为患病者本身的错误,患病者从“受害者(Victim)”变成了“应得者(Deserve)”。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这些意义、隐喻对于患者没有丝毫好处,只能引起羞愧,甚至于自我否定,只能加重患者的病情。桑塔格认为首要工作就是祛魅:“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最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看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五、阐释与反对阐释
《疾病的隐喻》旨在将疾病还原为疾病,不带有任何意义的看待疾病,延续了桑塔格“反对阐释”的批判思想。早在代表六十年代气质的《反对阐释》()一书中,桑塔格就直言不讳“阐释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这种对意义即“影子世界”(柏拉图的概念)的趋之若鹜和穷追不舍,令桑塔格反感。
在桑塔格看来,自古以来对内容的迷信般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ecosway365.net/xjyzzbx/78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