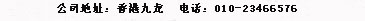北大毁了我
北大的通知书,是我在童年生活过的乡村里接到的,就在我的小学不远处。雨天的大信封有点潮湿,有点褶皱,我把它放在副驾驶,一路上都能用余光看到,在细雨蒙蒙的路上,我流泪了。
我大学考进了一个平平的本科,被调剂到市场营销的专业。我不知道这个专业对我而言是不是一种讽刺。在开学军训中我就有直接退学、去北大旁听的想法,这个想法持续发酵,为此和父母长相争执,最后的妥协乃是因为父亲说,保留一个考研资格吧。
北大情结,好像我们从小都有,小孩子都会说我将来要考清华北大,要当科学家,当哲学家,只是我一直带着这个情结无法摆脱。既然大学未能考上,终究还是想去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一番。
大一的我,在校园的湖边、楼顶,抱着尼采难以释怀,雨天都扛一把大伞放声长读《查拉图拉特拉如是说》,我不知道为何会接触到哲学、接触到尼采,但它们当时确确实实地点燃沸腾了我,让我始终有一种想打破的冲动,我不知道要打破了什么,要毁了什么,但就是在酝酿准备着。
直到大一结束,我脑袋里突然鬼使神差地驻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一边请假,一边去北大旁听。如此简单,却如此精妙之极。
带着这个兴奋,我居然还找到了校长,恳求他放我去北大游学,校长有点好笑却又满目慈祥地对我说,“等到毕业吧,毕业后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可是我如何好将青春交付蹉跎?沮丧的我躺在荷塘边的长椅上,一声鹧鸪啼时,才使我想到也许可以请病假,假病假。
医院有很多朋友,或许他可以设法开到假病历。姑父万分支持我的想法,他说,北大一日自然胜过在此十日、百日,如此便去得。他设想要开这样一种病例:既不传染人、不引起恐慌,又看不出病症,还需要长时间休息。他很快找人给我开具了“急性肾炎”,医嘱静养三个月。
但这个病例并不能用来请校假,因为校规规定,事病假超过一个月则要求休学一年。而一年的一个月,又远远无法满足我的游学期望。无奈之下,只好一一欺骗我的每一个任课老师,说我不能请校假,因为会导致休学,只好求老师通融,可以不要平时成绩,保证自学并参加考试。
最后一关,是辅导员,若跟他摊牌,很可能会导致从此被“监视”,若不摊牌,纸里又包不住火,计划随时会在败露时被终止。而况,辅导员有任何理由或必要同意这样一桩违纪的事情么?随便一两句官方话语就可以把如此荒诞的行径判处死刑了。
终于是天欲助我,大二伊始,我的辅导员换成了一位干练的年轻姑娘。我母亲找到了她,诚恳地与她沟通,恳求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证我随叫随到,并保证父母对我的监护。
这种违反校规校纪的口头承诺是没有任何效应的,但辅导员凭着她的直觉和对我们的信任,竟然甘愿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放我走!她全力支持了我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没有她的胆魄和胸襟,我的计划大概只有流产的宿命。
大二至大四,近四十位任课老师无一例外地同情了我这个骗子,他们的善良使然,全都没有苛扣我的平时成绩,而我也无一例外地顺利完成了他们的考试。只是有个别老师不时忘记了我这个“病人”,反复点到我的名字,当堂大问,这个王磊,怎么总是不来?这个时候,班长就会帮我大声喊“他腰子发炎了,住院呢!”几个班的同学哄堂大笑……一两年间,我给人的印象都是腰子不好。
而就是这个腰子发炎的形象都是班长为我精心设计的。对于肾不好,大家会一笑了之,但对于旷课不上考试照考,还去什么北大游学,大家则不会一笑了之的。对于出逃计划,我们秘密守之,三年间,我以病人相示。
刘班长是头一个知道我越狱计划的,我一想出来就在和他商量了,当时我们站在寝室楼顶上,自夏入秋之风鼓起我们的汗衫,像饱胀的船帆,他慷慨地倾听着我的激昂,最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成功,只许成功!似乎是我要带着他们的梦想一起远航了,只是他们没有我幸运,我在北京有一个家。
但这个家起初并不在我的计划中,我和父亲偷偷商量之后,不敢向母亲坦白。虽然父亲只犹豫了半个小时就支持计划了,但我们都知道母亲可能为此要纠结好几个月都不会同意,所以父亲设想给我在北大附近租个房子。任何一个母亲最初都很难同意如此,她们会以为那是荒废学业,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还会因为违反校纪而失去,还会担心我半路变心、决定再也不回本校。
大一暑假我回到北京,反复考虑之后,觉得瞒着母亲终不是长久之计,便坦白相告,结果母亲果然大动肝火,甚至以流泪相逼反。我们和母亲的谈判整整胶着了两个月,这是计划中最为艰难的部分。我不断争取权威的认可,最后由于得到了高中校友、北大法学院院长助理的首肯,母亲才放松了纠结,并且在大二开学后,主动陪我找辅导员谈判。
除去大二上学期尝试性请假一个月,其余五个学期都是请假三个月,每个学期只在开学一个礼拜和最后一两个礼拜在本校完成开学和复习考试事宜,其余时间都在北大。
我的病因后来也改成了“慢性心肌炎”以挽回我肾不好的形象。姑父给我开过的假病历,我至今都珍藏着,因为它们不啻于是入学通知书。
当年11月7号,我的K从芜湖开动发往北京时,我豪迈地觉得一个时代开动了。11月8号,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子涌动的北大,金秋银杏落叶,厚厚地甸在校园路上,我开始了对它五体投次地朝圣。第一天回家路上我哭了,因为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如果我早些体会到这一点,那么在高中的学习也就不至于那么夹带着启蒙地叛逆了。
旁听的历程里有被排斥么?当然有。我开始旁听的第二天,在二教门口看课表,找到标注文、史、哲、政、经、法、艺的就准备去听,看到身旁有学生在看课表,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在找自习室,以为也在找课表,便以为找到同道,问:“同学,你也是旁听么?”他说,“你怎么这么问?你是旁听么?”我嗯了一声,他便说,“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旁听的,不参加课堂讨论,不作研究不考试,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话真是惊了我一身汗,但这在北大是绝无仅有的,处得越久便越知道它的包容与敦厚,而其中鲜有的刻薄,也必然是犀利的、针对问题的。
游学者的问题正在于,我们不参加课堂讨论,不作研究不考试,所有正统重要的学术训练,我们都错过了。但北大陶冶了我们的胸襟与情怀。
孔庆东说,“什么叫北大人?只要被它的精神感染,哪怕是在学校里扫地。什么叫一流大学?就是有很多人坐在地上听课、就是校园里的猫敢四脚朝天睡觉的大学。”
孔庆东无论是讲鲁迅、老舍还是金庸,课堂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室换了大的再换更大的,但他还是被堵在过道里,上课好几分钟才能挤进来,讲台讲桌下都挤满了人,只给他留个几步开外的周旋空间,那种课堂上,你就问身边的人吧,十有八九都不是选课的,一半都不是北大的,连周围附中的高中生都要来蹭课。
那什么叫“猫敢四脚朝天睡觉”呢?就是猫不怕人,完全不戒备,或有觅得供职、给光华看门的,或者出入佛老、去教室听先生讲课的。
每年自秋入冬,图书馆和文史楼之间的路上都会摆上一捆捆的树枝,渐渐才知道,那些树枝是为喜鹊筑巢准备的。这种对动物的温暖表现得如此稀疏平常,故燕园的喜鹊都悠闲自在,显得格外典雅绅士。
偶尔在湖边,远远看到杜维明先生拎着好多书,穿一袭黑袍子,很像是霍格沃兹的教授,在秋风落叶中缓缓走过,那道景色在园子里最是使人神往。
未名湖并不总是明澈,真是非良辰不美景,只有配些好的风、好的雨和雪,好的天色,湖面才与四野之光景交相美丽起来。这个时候,想到那句“未名湖是一片海洋”,会油然感喟,嗯,是如此的。但天下的池子,在京城就成了海,在燕园就成了洋,全在看它人的胸襟吧。
就在这湖边,听陈平原老师讲过,有一回他和钱理群还有其他几位先生在湖边漫步,平原问他们说,假如是世界末日,你们还想做什么?钱理群先生几步未抬头,半响说,我想再给我的学生上一节课。在旁者哈哈大笑,但看到钱先生分外认真的样子,就笑不出了,被他的、其实也是大家共有的这种情怀所感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得之,我幸,不得,我丧。而被天下英才教育之,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
吴飞老师讲过,他曾经在离开北大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坐立不安;戴锦华老师说,在她读北大时,对它有很多的不满,同学挥斥方遒似乎腔子里总有发泄不完的愤懑,但是直到毕业很多年以后,才发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从根本上养育了自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日后安身立命的根本;孔庆东说,北大人何以不同呢,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喝一碗好酒打底子,以后就不怕寒邪,从北大毕业却又是孤独的,似乎再找不到可以对话、可以置放灵魂的地方,但是诸位,五四中有多少呐喊的青年后来成了革命的叛徒、成了别的贵太太,你们将来是是像《狂人日记》说的终于好了,还是没好,全在诸位自己。
在每年那个特殊的日子,靳希平老师会在讲桌上点上一颗粗壮的白色蜡烛,默默地如常授课。在海子的忌辰那天,梁文道曾做过一个讲座,讲到契诃夫: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在面对人民的苦难时一种不人道的奢侈,他决定救赎,他要穿越整个西伯利亚,到库页岛去,到沙岛上去,那里积聚着所有被流放的难民。他带着一瓶极其珍贵的白兰地,一瓶装在水晶瓶子里的法国白兰地。当他经历了很久很久,亲历了人间地狱,在行程的最后,他打开那瓶无比珍贵的白兰地,取出天鹅绒布里包裹着的最精致的银酒杯,打开,斟满,喝下一口,作为对自己的犒赏。
我总说,这些年,是北大的每一滴水养育了我。数年厮磨,饮于斯,用于斯,乃至生于斯,长于斯,没有缴过一分钱,老师的资料照样发给我,学生的座儿我不惭地坐着,甚至中秋节的月饼都会发到我手里。在这里,我结识了好多师友,他们成了我生命中分外重要的人。在那些还格格不入的日子,是你们给了我归属感。
我头一次从北大回本校之后,骁发短信来问,“啥时候回来?”那种温暖竟是热汩汩的,好像我的归宿在北大,而非别处,一句啥时候回来,就好像把我引为同学同志一样。骁总是那个率先问候我的人,今年过年,我终于抢在他前面把电话打了过去,大笑说终于第一次抢先了。而在我们温暖的友谊中却有过我的一段时间的冷漠,那是我第三次考北大失利,迫于形势,不得不上班,那阵日子,觉得简直永远脱离学问了,也自卑地觉得我和他们渐行渐远了,很难再打电话再见面去讨论学问,哪怕是说说闲话。但还终于是骁,他给我发短信,问“最近在读什么书呢,都还好吧?”一时间百感交集,那种开始脱离钟情梦想的人都会有这种百味杂陈的感受吧,特别是看到曾经的伙伴仍在舞台上向你招手,把你从坐席上牵上舞台,再跳一支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会哭么?会的。这是所有有梦而不能者的心伤。毕竟很少人有条件和勇气足够坚持自己的梦想。我的这一次“叛逃”是被朋友们拉回来的,他们说我显然是书没有读完的人。
那些年在学校,从课间对老师的尾随追问,到因为李猛老师在黑暗的走廊里叫出了我的名字而窃喜,从三年爱而不敢相近,到少闻先生请我们全家吃饭而兴奋不已;从学智先生第一次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到面试时他作为组长时对我说你来了啊;从文轩老师走到我身边看我用毛笔记笔记,到我去中原先生家里吃他种的葡萄;从人人网上的相识,到因晖临、重庆先生始,引过近五十位老师到我查济的家中开会、读书、考察。
这儿就是如此展开怀抱的,我也是如此奋力地拥抱它,那些年,在暗恋它时,就暗暗许下心愿,终有一天,要明媒正娶,要在进门的时候不登记身份证,而是亮出那张橙色的校园卡。终有一天,我要把在这里得到的,尽最大的力量作为回馈。
我说北大毁了我,毁是重生的意思。
第二部分考研
今年过年,我在县里的宝胜禅寺求了一支签,问菩萨考研结果的事情,签上说“当初得意反成失,如今忧危事不危。若得故人相接引,千年枯木再生枝。”表弟说,千年枯木,是我奋斗了千余日,该要收获了。
如果说北大在我的心底播了种子,那么从挣扎出壳到成长发芽,直到可以接受阳光雨露,也许是艰辛的,也许是快活的,但我也许恰恰是一颗身上压着瓦砾的种子。
如果我的求学之路没有一开始泛观博览式的通识学习,就不会有后来对中国哲学的情有独钟;如果求学之路终止于游学,而没有后来的四年考研,三年失败,那么至此的人生或许要娇气得多。四年间,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我担惊受怕,承担了实际上最苛重的压力,我的北大的朋友们,他们承担了我的全部指导牵引工作,如果没有这些物质的、精神的、战略战术的全面支持,我举步维艰。在这个集体的行动中,我只负责撞倒南墙不回头以及把屁股粘在凳子上。
我之所以说自己是压着瓦砾的种子,是因为我的脑袋并不那么好使,却还喜欢喜欢思考问题,很难把要考试的东西当作知识去消化,总是率先把它当作身心性命的东西,当作永远需要思考的东西,当作需要厚重积淀的东西,
起先读圣贤书,对我而言,用毛笔抄一遍是最起码的尊重,因为我没有一目十行的资质,只能“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越来越不敢说,我读了多少本书,真要图个数量,我只说,四书、理学抄了多少遍、诵了多少遍、读了多少遍。经书上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句子,只几个字都够受用终生。
我常以为,“大器晚成”四个字没有任何炫耀和曲意,“大器”没有更为优越的意味,不过是一个更迟钝、笨重的器,而“晚成”也没有安慰的意味,只是说,“大器”的锻造必然要经历长久地陶铸。我也常常这样勉励自己:李安在家中“窝着”的那六年也许是对他人生最有价值的六年;文革十年,淘汰出真爱知识和真理的老三届;玄奘在印度留学了十七年;朱熹修四书章句集注近四十年。
其实第二次考试我就已经达线了,但是未进复试,结果可以有不少不错的学校可以调剂,但我想都没想就放弃调剂了。母亲为此想到辄流泪,她不想看我那么辛苦地坐读下去,那时已经把皮椅子坐穿了,滑轮也坐断了。后来考研的三年,我主要都在家中复习,母亲每天给我端果盘,不敢打扰,看我从天明学到午夜,日日如此,夜夜如此,不出门,亦无太多交际,简直像要入道一样,有时候学得太安静,她都会悄悄进屋看看我是不是睡着了。家里并没有经济上的负担,让我再脱产学习多少年也没有关系。母亲只是担心,我这样是不是够得太高了,是不是没有这个资质,会不会把身体学垮,会不会精神压抑,她每天拖地时似乎总要低头不经意看看我的桌下,看看是不是有很多碎头发。这些都是一个母亲担心的问题。
我第二次达线的那天,母亲并不在家,她下飞机的时候得到我达线的消息,她说,从旋梯上下来的瞬间,特别的自豪,母亲发短信说,儿子,谢谢你!但第二天,母亲就得知我并不能进复试,而且我当即决定不调剂,母亲面对窗台流泪了,悲欣之间,如此而快,我揽住她,说没事的,一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时候自己会怀疑自己,有时候父亲会怀疑自己,有时候,他会说出我很难接受的话,有时候他又无比信任支持我,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摇摆着坚定着,都在守望相助地捱着分外艰难的日子。
在我的书房里,我画了一小幅油画,画上鲁迅抽烟望着黑暗无边的窗外。他那种忧患中的刚毅给了我苦闷中的安慰。我每夜最大的轻松就是打开窗子,伸展躯体,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偶尔看见过流星划过,我就对着天空说,麻烦你,让我考上吧。
随着失败的累积,我的地位越发尴尬了,第三次失败以后,我整个家庭都不知所措了,正好逢着北大的龚鹏程先生叫我去他那里上班,龚先生厚爱,但我在那里浮生三月,失魂落魄,我都以为自己要永远离开哲学、离开北大了。那阵子总是开车接送龚先生来往北大,在哲学系的四合院旁的中文系等着他,在理教、二教等着他,看学子往来,我却俨然是个司机的样子,茕茕孑立,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不禁悲从中来,原来再多少风华攒下了风骨竟也如此容易凋零,原来无名无份是如此的没有存在感。
而那最可怕的,不是黑暗,而是灰色,是不温不火中,忘掉了初衷,甚至找到了足以反抗终极理想的理由,我甚至渐渐开始厌学,觉得功名何有于我哉,如果不是师长在悬崖边对我的最后援手,和有人在转折点给我了极大的刺激,谁知道我会不会峰回路转呢?
当我决定辞职披甲再战时,父母仍然是支持了,母亲仍然给我端果盘,每天我对母亲说,谢谢!她说“我欠你的。”我也说“我欠你的。”
我也偶尔出门散步,也偶尔和朋友欢聚,那劳作间短暂的消遣竟是那么愉悦轻松。
凳子依旧要坐穿,书依然要翻烂,但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却是有泪,有汗,有一个关于初衷的梦想,如此痴心迷醉,如此不知悔改,正是你,毁了我。
年夏王磊
王磊
转载请注明:http://www.ecosway365.net/xjysp/8116.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