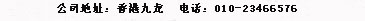书生的有用和无用周教授的人生路大使
笔者问:上次说到被分配到农场接受再教育结束了,马上又被分配去四川山沟里,这是您的第二个低谷是吗?
周老师答:是的。年8月的一天,我一路奔波(四日三夜)去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新添乡国营长庆机器厂报到。说是机器厂,实际是五机部(现为兵器工业总公司)属下的某兵工厂。
长途汽车一路摇晃几个小时快到厂门口,突然听到,“周仲安,老周!”奇怪,哪个人居然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到!探出车窗一看,是我丹阳湖农场同一个班的“战友”。“别下来,别下来。回去,回去,跟着车原路回去。”他边跟着车跑,边对我喊。我下车,他一把抱住我,想抱我回车里去。“太苦了,太苦了。你这个上海人受不了的。为了拦住你,我已经连着三天等着这趟班车喊你的名字了!”
回去?你说说容易,真回去,我不是不服从分配了吗?!这顶帽子吓人哦!
在厂门口喊我回去的“战友”问:那么怎么个苦?
答:进了厂门住下,就领教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领袖的这个指示一下把原在重庆的一个车间移到了这个偏僻隐秘的山沟里。我和几个差不多时间分配来的大学生,被安排在厂区里面机关办公楼底层一大统间里。
吃饭上食堂,要不自己弄。记得我第一顿午饭自己做的情景:搪瓷杯子里一把米,淘好加水,放入从上海带来的一根香肠,到办公楼后面的一个灶上隔水蒸。到时取出,杯盖子打开,一股腊味扑鼻而来。这时,原在灶台附近堆泥垒石建屋的几个民工呼的一下围上来:“啥子哦,吃啥子嚒,拉么香!”我问他们吃什么。“红苕(红薯)。”
带来的美食总要吃完。去食堂吃饭的第一顿来了。我把手中的搪瓷碗递入窗口。“要啥子?”“你有啥子?”啪,碗顿时堆满。四分钱。是什么?藤藤菜,即蕹菜。因其粗壮,又被赋予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名:无缝钢管菜。菜里不见一滴油,老得不太好咀嚼。“粮多猪多肥多。”顾名思义,粮食多了,如玉米等,可以喂猪。猪多了,猪粪也就多,施于农田的肥料当然也多。
办公楼
这个时候,文革如火如荼中,四川的武斗还有余波,这样的形势下,粮食供不应求,猪肉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厂门口有块空地,平时毎隔五天,供周边的农民拿上玉米、红薯、藤藤菜、棒棒菜、鸡蛋鸭蛋、公鸡母鸡阉鸡、鳝鱼鲫鱼,甚至皮包骨头的小猫咪,翻过山头,来这里摆摊互通有无。在机床边干活的人没法离岗,能走得开的,全瞅准机会,溜出去买或用粮票换所需要的,顺带着再到宿舍家属楼自家屋里兜一圈。
吃住再苦,工作得干。“抓革命,促生产”嚒。这个指示读上去容易,具体怎么落实就有点挠头。“宁左勿右”保险,那先抓革命。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
要开全厂大会了,大家各显神通,拿着可以垫屁股的家什,到这个所谓广场上席地而坐。后来厂领导决定为每人做个小板凳。有大会,一定有小会,而且更多。上下午上班,先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唱革命歌曲,甚至来一段《智取威虎山》。山沟闭塞,为了调节,工会组织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或以车间科室为单位搞文艺会演。
广场上开大会坐的小板凳伴随周老师至今
这个时候,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这是我的工作单位,在这样的地方扎根一辈子不敢想,也不愿意。但想一年半载就离开,也是痴心妄想。既然如此,我先改变自己,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想起入大学的第一年,我天真无知,被鼓励去了复旦大学话剧团。演了两个话剧,全是龙套角色,一句台词都没有。部队农场里,团部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小分队),去附近农场表演。队里有两个上外的女同学,善舞不善歌,偏要拉上我去为她们伴唱,说我唱歌有感情,我歌声响起,她们跳起来“入情入戏”。
天地良心,我唱歌音不准(后来一唱就走调,到现在也是。)她们说“没有觉得”。既然受过这样的“文艺”熏陶,我就在科室里“活跃起来”。样板戏不会,“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这样的会。
我从让科室的人学唱,到排革命歌曲大联唱和诗歌朗诵,再到领唱,甚至指挥,样样来。我还参加乒乓球和象棋比赛,“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了。土得不能再土的主席台上,经常有我的身影。我成了厂里的红人。
科室人员集体照
现在回头看,再兮格格不过,但这样“阿戆”的作为,充实了我的生活,至少在白天。现在想想,心态能否放平,全在自己。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睡眠障碍自那开始。周日,各家各户煮饭烧菜,一起分配来的,不少谈婚论嫁起来。
我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这个时候,食堂伙食稍有改善,十天一次供应三两肉,当天吃完。一天,面对九天以后才能再相会的肉片,特地去买了一瓶泸州大曲。本不会喝酒,心情又郁闷,酒喝了几口,肉吃了最多一两,居然酩酊大醉了!胸中的郁闷,伴随着呕吐,喷薄而出。
厂里日子待久后,情况了解多了。原来这个厂被安排了一个援外项目——给叙利亚建一个生产同种类产品的厂。因为所有产品图纸和有关设备的说明书得提供英文版本,五机部就从丹阳湖农场抢了我们几个来翻译。我去的时候,专家组还在那里考察,这里只是在做准备,所以没有什么要翻译。我被安排去写仿宋字,在图纸上写“光洁度”之类的词语。
就在如此这般打发时光之际,科长突然通知我去北京部里出差。去北京,是个天大的美差。我当晚出厂,天亮到成都。然而要去北京,难了。那个时候,买一张从成都到北京或上海的火车票,不排上几天几夜休想,更不要说卧铺票了。患难时刻见真情。我人生道路上又一”givemeahand”的人出现了。
这前,先得介绍一下我读研究生的另两位同学:翟象俊和夏孝川夫妇。他们是陆谷孙先生的本科同学,现在一起读研。翟老师的英语以简洁、精准著称,与陆的风格不甚相同。而我,受他的风格影响更多。他谦和低调,与陆亲密无间。夏老师则心直口快,大方大气,我们中,也唯她会偶尔“怼一下”陆。对我这个师弟,她十分关照。知道我要去四川后,就说:“要买火车票,找我姐,她在铁路局工作。”我知道她有个姐姐,但从未谋面过。
后排左一是翟象俊老师,前排右一是夏孝川老师
这次,我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大早,我找去。“知道了,孝川跟我说了。今天住我家头。明天走。”夏老师的姐姐话不多,信息清楚。第二天,她给了我一张票签,纸条又小又薄,我容易出汗的手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化掉。所谓票签,即贴在车票背后的一条纸,上面印着几号车厢第几位子。如是卧铺,印有铺位号及该号的上中下铺位。她陪我去售票窗口,让我付款后,帮我拿上硬票,送我进站上车。
自那以后,从成都到北京,从成都到上海的火车票,全她包了。偶尔我要得急,或者一时间没有票,她陪我进站,把我交给该车次的列车长,让他为我上车补票,如果车上铺位满坐,就安排我在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多少年,多少次!这样的大姐,忘得了吗?!
图片来自网络,摄影师王福春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去叙利亚的考察组回来了,组长对部里选派的翻译非常恼火!在考察组动身去机场飞叙利亚大马士革前一刻,被指派为翻译的小伙子在招待所里面壁而立发呆。“走了,快上车去机场。”“我不去,我不会翻译。”哎哟喂,这是什么时候。不去也得去,“我们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去了学呗!”有关人这么指示。组长听到这段对话心里有数了。
到了大马士革,叙方和我驻叙使馆有关人员在机场迎接,组长一一介绍团队成员时,说小伙子是秘书。使馆人员一听,胸闷至极。“名单中明明没有秘书,接下来翻译由使馆的人来做?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有多余的人手?这不是添乱吗!”
这个不会翻译的“翻译”没过几天被请回国了。他也高高兴兴去干他的本行:X光探伤仪操作工。他确实是学英语专业的,还是川外毕业。只是他进校不久,文革开始,四年后分配去了重庆的军工厂。吉普车停在他成都郊区家门口的田埂边指派他去当翻译的那天,他刚回家探亲看望妻女。
考察组组长正为这件事气得拍桌子之时,“来组长,给你推荐个人,刚来我们厂。复旦大学研究生。”就这样,等项目上马,需要翻译时,我被派上了。
引荐周老师给组长的工程师蔡佑斌
问:虽说个人无力挣脱时代潮流,但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在复旦求学,第二个黄金时期就是来到了叙利亚吧?
答:年9月12日,一架巴基斯坦航空飞机,由北京飞卡拉奇,转机后前往大马士革飞去。我人生又一页开启。
我的身份是援外项目翻译,整天下工地,为我方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语言服务。一天,使馆负责援外的二秘电话来组长,让他带上我去使馆。由于经贸处的阿拉伯翻译回国度假,与叙方的一年一度的贸易谈判由我翻译。
谈判结束,叙方官员特地送我们到电梯口。与我握手时,他突然使劲摇着我的手说:”Thankyouverymuch.Youhavedoneaverygoodjob.”这句话,经贸参赞听懂了,他向大使汇报说这个小周有水平,可不可以让他留下……
叙利亚工作期间在其地中海海边度假
年国庆节,使馆如常举办酒会,叙有关政府官员和各国驻叙使馆代表应邀参加。整个气氛融洽和谐,谁也没有意识到不出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情——埃及和叙利亚于是年10月6日,突然袭击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
中东第四次战争爆发。当天阳光明媚,四周一片宁静。这个气氛怎么也没法和战争联系得上,何况这个月是穆斯林的斋月,那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故这场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
问: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只在电影里书本里知道战争。您亲历战争,做了些什么?害怕过吗?
答:我和使馆里几个年轻人跑到七楼楼顶看热闹,刚抬头,忽见远处一连串炸弹往下坠。使馆党委指示所有人员全部下到底楼(没有防空洞),会开车的去买大米、面粉、电池,其余人挖泥,装麻袋面粉袋堵大门,当天完成任务。之后,没有大使指派,除新华社记者,谁也不得走出使馆。
6日开战,26日结束。期间,我做了谁也没有要我做的一件事:收听叙利亚,埃及,以色列,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然后整理成战况报告。大使吃早餐,这份报告即呈现在了他眼前。事后武官说:奇怪,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要做、能做这件事!
那个时候,子弹火箭不长眼。停在港口的船只随时都有被击沉的风险,各国船只都着急地想获准离港。国内来电,广州远洋公司一艘货轮泊在拉塔基亚港口,得立即让其离开战区。使馆党委立即决定,由一名随员与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馆全权处理。
去的路上,叙军军车坦克往南开去,民众情绪高涨。我曾亲眼目睹叙方用苏联提供的扛在肩头的萨姆6导弹击落以色列一架战机,飞行员跳伞,老百姓拼命跑去捕捉。带着《人民画报》等,我们两个与叙方港务总监强烈表示,中国人民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任务圆满完成。当晚我们在港口酒店住下,准备第二天精神饱满地凯旋而归。
半夜三更,密集的火箭弹爆炸声把我们警醒。果真,以色列海军从地中海的军舰上向拉塔基亚发起袭击。在睡梦中被惊醒本身就不是件舒服事情,更何况火箭弹导弹在我头上呼呼地乱飞,要我不害怕?做不到。躲在酒店存放物资的地下室里,我确确实实浑身抖个不停。
晨曦到来,外面出奇的安静。我们赶紧往回赶。这个时候,与来的时候,形势完全不同。兵荒马乱不至于,但一路上,被炸后的炼油厂浓烟冲天。加油站几乎没有油供应。我们两个拾了一根棍子和几块石头放在车上以备不测,更想方设法凭外交车牌,向叙有关部门申请到加油的配额。所幸回程多是下坡,当我们行驶到使馆门口的时候,只见大使亲自带着馆内人员给我们来了个夹道欢迎。
第二天,大使说:小周,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他平时不大说话,真的熟悉了以后,我与他几乎没有了大小。打乒乓球、下象棋,我都没让着他。大使夫人是使馆办公室主任。一天,她说:这个柜子的钥匙你拿着。我打开一看,全是书。
这个时候,国内革命形势有点变化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应邀到北京举办交响乐音乐会。恰在这时候,奥地利驻叙利亚大使馆大使来拜访我们的大使。两位大使言谈甚欢,谈及了北京这场音乐会和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家及其作品的话题。谁翻译?我。临走,奥地利大使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想到,你们中国外交官员对西方古典音乐都那么熟悉,欣赏水平这样高。
驻叙利亚大使馆馆内合影。女士是大使夫人
在叙近两年半后,我回国成家。接下来,有关人士应该兑现承诺,安排我到五机部驻上海的援外组工作了。然而……
我重回原厂。回去后,真的没有什么事做了,因为该厂承担的援外任务已经完成。
问:深受大使的喜欢,工作能力又受到大家认可,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回家乡,又被打回原厂,有一种从云端跌下来的感觉,是不是心灰意冷了?
答:何止是心灰意冷!隔年,在家休探亲假的一天,我心脏突然乱跳:室性早搏频发,病毒性心肌炎待查。住院治疗十天出院,获休息一月病假条一张。我大喜过望,居然可以在家多待30天了。而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仅仅12天。一个月后,医嘱继续休息一月。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病魔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早搏再度频发,手麻,脚无力到难以动弹。这次住院不是十天八天了,住了近三个月。
年起,我开始“吃劳保”。所谓“吃劳保”,简而言之,“靠劳动保险过活”,相关词语是“泡病号”,工资打六折,编制打入另册。我一下从大使先生的翻译变相为“无业人士”了。
第二年的某天,收到急电一份,是厂军管会发的。电文如下:“接电速回否则后果自负”。我回电云:“有何后果可负请告”。也许有人会问,我当时怕不怕。人跌倒到地,就剩头上一爿天。对我,除了一条命,剩下几何。
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谁能预料旦夕祸福?
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号召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山沟工厂与全国各单位一样,都在学习大会文件,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厂里有人提及:我们这里有个知识分子,在他身上落实落实吧。私下,另有人来信让我赶紧回厂,人不在,大家再呼吁也白搭。我赶紧回去。人事科科长一见我就说:你不是要走吗?放你,自己去找单位!他这个口气,不相信我能找到单位。
问:现在要落户上海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是不是更难?
答:要找有户口配额的单位接收谈何容易!我马上回到上海,向尚在筹建中的金山石化,宝钢发去申请。上海不行,我退而求其次,去苏州无锡也行。那是个黄梅天,雨过天晴,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我,由我大哥陪同,离开苏州铁中准备去无锡。
看不到半点希望的我,身心俱疲,突然不想去了。在打道回府的列车上,我兄长偶遇一朋友。从此人口中获悉,中央为尽快恢复生产,铁路运输先行,其中一条措施是恢复铁道部驻上海物资管理办事处,让上海给予户口若干。
巧的是,我兄长之前曾在该单位工作过。“写个简历看看。”该处党委书记回话道:“这个人要了。”书记看了我的简历,布置人事部门收下我。一句话,连标点符号,总共六个字符。
这个单位是搞物流管理的。这个行当之前听都没有听到过。我对书记说,我什么都不会,让我当个秘书写写东西吧。“不需要。党培养了你那么多年,英文不要忘了!”他设置了一个科研室,自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副科级)。级别有了,住房也解决了。“安心看书。”他说。人家在忙,我安心看书?我不安。
一位工程师看出了我的纠结。“周科长,我们一起去上海图书馆,把国外有关立体仓库和电子秤杂志上的照片复印几张怎样?”我把资料借出,发现文字显然更重要,复印照片谁都可以做。我去上图几次,复印了不少文章,随即埋头翻译起来。不仅翻译,我还自作主张编了一份杂志,取名《物资储运》。
书记见了大喜,立马带去铁道部物资局汇报成果。在这个行业里,这样的杂志是首款。后来物资局组团去加拿大考察木材防腐技术,点名我为翻译。本文第一集提到的那个英国工程师就是这样遇上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外文系让我回去。“回国后我想回学校教书。”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我与铁道部物资局领导说了的,现在复旦让我回,我应该巴不得才是。可我没有忘,人家可是给了我户口,安排了位子,还解决了住房。
我迟疑不决之际,接到了一个“周仲安,侬有啥了勿起。复旦有的是人才,现在三请四请侬,侬架子倒大的!”说话的是我在复旦求学期间的老领导。这显然是个激将法,我一下子被将住了。
“走,欢送。留,欢迎。你自己决定吧。”单位书记扔下这话转身离去。望着他的背影,我感慨万千。就这样,我回了复旦,教师生涯由此开启。
真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周老师几次落入谷底,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学识和才华总会让伯乐相中。他是学英国文学专业的,为何翻译起工程、技术,音乐等专业性如此强的领域也那么游刃有余?回到复旦,还有挑战吗?续集有没有,要看老师讲不讲了?!
妙心台
一个致力于缓解国民焦虑的图文平台,
如果你喜欢我们所分享的文章,就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ecosway365.net/xjysp/6829.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